《吞噬太阳的女子》剧情介绍
《吞噬太阳的女子》长篇影评
1 ) 折磨人的爱
Sokurov的《父与子》参加了2003年噶纳电影节的竞赛单元,呼声不高,反应平平。
但是寥寥数语的简介吸引了我。
“他们是父子,有些时候他们像兄弟,有些时候他们像情人……”父子恋?
回想Sokurov那部几乎将我窒息的只有60几个镜头的《母与子》,被人捏住喉咙的感觉再次来袭。
然而,不得不说,一年多来,盼望的就是这个被称为最有塔科夫斯基相的Sokurov的暗含禁忌题材的作品。
我相信,绝不会出现《滑板公园》中那赤裸直白地丑陋冲动,而必然是一如既往的诗歌的流淌。
影片一开始,是黑屏,画外音是令人不安的喘息声与肌肉击搏声,接着暖色画面的出现,浮雕般的身体流动着,像在海洋上颠簸。
那种律动那种渴求,都难免不让人遐想,可声音却是两个男性的。
一张无助后释放的嘴,是夸张处理的镜头。
终于画面安定下来,中年男子怀里搂着一个少年,对话依旧暧昧不明:“你又救了我……我快被他们吞噬了……”“下次,你就大叫,否则痛苦会吞噬了你……”少年贪恋着男人的爱抚,断续地说“我……爱你……”而男人微笑着,抚摩着少年的头,随即,出现了超越时空的镜头——男人望着镜头外问“现在你在哪里”,少年出现在林间小径上,梦呓着“这里只有我自己……” 的确,男人与少年就是那对父子,居住在小城某处的阁楼上。
逼仄的空间内只能容纳两个人的灵魂相偎依。
这段梦幻般的画面后,是两个妇女吃吃地笑,仿佛偷窥到父子俩隐秘的心境。
女性,是这个世界中缺失的。
父亲到儿子的军校探望,儿子Aleksey这才第一次正式亮相,是个穿迷彩的俊秀小兵哥,有羞涩的笑容和清澈的眼睛。
他亲热地与父亲拥抱。
此时女友Marina也来探望他,两个少年隔着窗棂对望。
镜头给了超特写,少男少女的美丽面庞被窗棂分割成局部。
Marina认为自己进入不到Aleksey父子中,而Aleksey反问“我为什么不能两个都爱?
”女孩子逃掉了。
在父亲面前,Aleksey用拼命训练掩饰失落。
重新回到蜗居,Aleksey似乎躲着父亲,他在自己屋中看父亲的肺叶的透视照片。
他伸出纤细的手指抚摩那些肋骨,企图抚慰伤痛(如果有什么伤痛的话)。
果然,父亲说,有到其他城市工作的机会,薪水也会高一些。
而Aleksey把父亲逼到墙边,一再表示“你不在我会很孤独”。
父亲战友的儿子Fedor从外地来访。
与Aleksey的强势不同,Fedor似乎过于温和。
他想解开自己父亲失踪之谜。
Aleksey没有让父亲把话说完,引Fedor来到阁楼外悬空的木板上。
Aleksey说自己最瞧不起胆小的人。
父亲发现了儿子耍弄客人的伎俩,有些恼怒,呵斥两人回屋,又忍不住教训儿子,Aleksey出言顶撞,最后二人竟至厮打起来。
隔壁Aleksey的玩伴Sasha来帮架,四人更是扭做一团,以父子俩的衬衫撕破告终。
Aleksey打发走Fedor,又从父亲处求得原谅。
在儿子明镜的眼眸中,父亲无意隐瞒,告之战友以身殉职的真相并叮嘱儿子保密。
Aleksey寻到Fedor,二人搭老式电车游逛小小山城。
Fedor的怯懦背后隐匿着敏锐的直觉。
他和Aleksey探讨有关浪子的寓言故事,惊异于后者幼狼般的伤感,觉察出Aleksey父子间诡异的气氛,于是离开。
两个少年都在怀想各自的父亲。
夕阳西下,Aleksey踯躅街头。
他在回家的路上去探望Marina,希望Marina能温暖他的心,但Marina拒绝了。
Aleksey倾吐昨夜的梦魇,并说圣人曾言:“一个爱父亲的儿子,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望着Aleksey渐去的背影,Marina喃喃自语:“你们毕竟不是兄弟,钉死的爱表示你不能平等地对待你身边的人。
” 仍旧回到阁楼,在天台上Aleksey向父亲抱怨Marina,并以破釜沉舟的架势说自己要到另外的城市去忘掉一切再回来。
这次,轮到父亲流露出孤寂的表情,“你走了我会孤独。
”而Aleksey玩笑般骑在父亲头上反驳“你不会孤独,你会……再结婚。
”此时父亲笑了,笑容奇特,仿佛戴枷已久的犯人重获新生,又如溺死之人抓住救命稻草。
父亲说儿子的面容极像他的母亲,所以儿子的允诺对他来说很重要。
Aleksey眼中闪过一丝心碎的哀伤。
他叫来Sasha,搂着Sasha面向父亲,意味深长又决绝地坦白“我很爱他。
” 儿子的眼里只有父亲。
入夜,Aleksey说胸口痛,那是他每晚梦魇的根结。
父亲只好放弃外出散步而护送儿子回屋。
然后,一段平行蒙太奇,父子两人,以相同的姿势相同的心情,在各自的床上蜷缩入梦。
也许是在梦中,仿佛初始的轮回,父亲走上白雪覆盖的屋顶天台。
Aleksey问“那里有我么?
”父亲摇头,“只有我一个人……” 只能说,没想到这部电影如此好,如此用情至深、隐忍不发。
于我,是随时随地都可投入进去。
油画般的用光,凝重的影像,严谨的构图,诗意的对白,明晰的人物,使《父与子》充盈着一股浓郁的哀伤、深情和近乎毁灭的牺牲气质。
无疑地,父子俩都是对方的唯一,而且在儿子身上更有体现。
Aleksey援引圣人描述的父亲之爱,急切地从父亲身上找寻“让自己受折磨”的痕迹;Aleksey承认自己当兵是步父亲后尘——他想要拥有和父亲更多相同的经历,因为面貌已然不同;Aleksey给父亲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对造访者的探究,Aleksey推脱说父亲肺部有伤不能回想旧事以免伤怀;Aleksey咄咄逼人,父亲闪烁其词;Aleksey婉拒了隔壁Sasha要搬来住的念头,即便是多年死党,也不想让他介入到只有他们父子的二人世界。
收音机总在播着无聊的消息。
父亲打开,儿子关上。
这是唯一与外界沟通的工具,在狭小的空间内显得无比突兀和无辜。
不,他们完美,不需要任何外界之物打破平衡,除非,天平的一方有意减轻自己的砝码,让自己从这难以割舍的静谧和谐中退出。
这一退,就不仅是抑制不住泪水般简单的伤痛了。
两个人的家庭,有无限的延展性;缺少了负责稳定的第三者,便将幻化出无数未来的可能全部抹杀。
Marina,自觉的退出;Fedor,被Aleksey赶走;Sasha,想进入却只能隔岸观火。
Aleksey深夜的梦魇,是惊呼“妈妈在哪里”的无助,还是恐惧自己“对父亲的独占欲到了只有将其杀掉才能安心的地步”?
两个人的家庭,注定要被打破重组,或许会派生出更多种貌似稳定的家庭形式。
父亲、母亲、儿子、媳妇,子子孙孙无穷尽矣。
然而,看似坚强的父亲,真的能放心爱子远离自己?
在儿子每夜自溺般的噩梦中,谁能用有力的臂膀给他无忧的睡眠?
不动声色的Aleksey,真的能够做到太上忘情?
为了父亲的幸福,自己远遁天边去接受继母的位置?
Aleksey并不贪心,他只是希望既能够被父亲爱,又能够爱Marina。
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感,一个是救生之水,一个是燃情之火。
他们是普通的一对父子,但又绝不简单。
没有任何父子能像他们一样有亲密无间的距离,没有任何父子能如他们一样忘我地爱着对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告诉他们“不要担忧,因为你们代表了最极至的父子之情,你们有着神话般的道德与尺度”。
Sokurov擅长探究亲情的终极。
《母与子》中,世外桃源的小木屋,儿子与身染沉疴的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的呼吸是儿子生存的唯一的精神支柱。
大自然的声响仿佛为这样的天伦注上赞美的注脚。
而挥之不去的惆怅,依然是影片的主调。
还有《俄罗斯方舟》,Sokurov大胆到只用一个镜头就叙说了俄罗斯的300年的文艺历史。
现实和历史不停转换,梦幻与理性相傍游走。
一个镜头一气呵成,的确令人神往。
但,那离我太远。
只有《父与子》,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情节进入它,成为父子浓情的旁观者,然后不可避免地被它感染,像一粒尘埃,嵌入其中;或是成为儿子的一道目光,凝挂在父亲嘴角。
——07.2004 美丽的MARINA,她说,“我看到你的父亲了,我走不到你们中间” 我觉得这片子的音轨做的就像是——在耳边低语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导演的某种想法。
还有,影片中,Aleksey一直叫父亲为“父亲”,而不是亲昵的“爸爸”。
“父亲”在俄文的应用中,向来是很严肃的,都是成年后的子女对父亲的称呼,一般情况下不常用,那会显得很“生分”。
而Aleksey和ADA的关系,实在是不像是该用“父亲”来称呼的。
是不是,Sokurov又有所暗指呢?
走火入魔ING. 《父子迷情》的成功,各国际媒体均将焦点与荣耀锁定在国际大导演Alexander Sokurov的身上。
其实看过《父子迷情》的人,也都会为电影中两位饰演“父子”的俄罗斯男演员Andrej Shetinin和Alexei Nejmyshev的表现赞赏不已。
摘了段有关演员的文字。
总觉得网上诸多介绍越发的哗众取宠。
片头那段戏,研究了一下,我认为根本不是什么“MAKING LOVE”,就是儿子做了噩梦,父亲去解救他——对付毒瘾发作的人不还得用暴力手段吗?
2 ) 爱越深,痛越切
“父爱就是虐待,子爱就是被虐待。
”这话出自一对亲密如朋友的父子的儿子之口,可见爱越深,痛越切,这是俄国电影大师亚历山大·索科洛夫带出的故事。
父亲给了儿子无限的爱,儿子给父亲回馈的是无尽的痛,这是我们常见到的事与愿违。
当我的儿子降临到这个世界,我就怕自己将来有痛,更怕将痛带给儿子。
我因知道而尽力,但不知道错误是否在尽力而为中?
从生死(《母与子》)到爱恨(《父与子》),索科洛夫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2008.5.24http://williamho.blog.163.com/blog/static/749549142008424101654407/
3 ) 離開白樺林
影片里儿子对爸爸的称呼,自始至终都是「父亲(Отец)」——一种显得有些正式却不那么亲密的称谓。
父亲,他总在尊敬他的父亲,可他自身又使与其的关系永远无法成为单纯的「父子」或者「朋友」——很难推断出是谁先默许了关系的变位。
片头的「丛林」之隐喻,私认为是索科洛夫在全篇里做得最好的一个镜头处理。
女性角色在这个家庭里是缺失的、「隐藏起来的」。
丛林,人类初始之伊甸园,却仅仅剩下男性单独存在,且非爱人,而为父子:父子关系便从此错位。
索科洛夫是一位典型的俄国创造者,他总不去明说、从不把一些话搬进镜头里,叫人去猜,叫人去真正地联想。
他的镜头里充斥着大量的远景和环境描写,铺天盖地的雪和了无生气的房子,他对于留白的描写带着很多古典时期的影子。
这点上塔可夫斯基也莫不如是。
儿子在军营里问女孩,我为何就不能同时爱着你们二者,女孩用眼睛回答他:男孩把爱也揉成一团,分不清爱的种类与面庞。
另一值得关注的点,影片拍摄实地似为彼得堡,可片里的父亲和儿子说,他本是为了这位青年而留下,他本可以去大城市谋求好的工作。
还要去多好的城市呢:莫斯科、甚至向西边走去?
导演都没有明说。
他把这座实实在在的城市,用朦胧的镜头雾化成了一座虚拟中的小城。
父亲最终还是在雪天里独自缩了起来。
这个场面我记了十三年。
没有其他的雪的描写比它来得更深刻,也更孤独。
年轻的士兵终将离开白桦林。
附上一篇外网俄文影评:http://old.kinoart.ru/archive/2003/09/n9-article16
4 ) 缺失
索科洛夫的《父与子》与《母与子》这对孪生片在影像上的高度统一与诗意将亲情之间的互动与暧昧进行了抽象的展现。
索科洛夫的片子毫无疑问是闷的,而且是相当闷,是典型的通过状态来推动叙事。
本片里每一次父子间的互动、对视都有着复杂的情感和解读性。
而从头到尾的金黄色色调也给影像赋予了暧昧感。
父亲是退伍军人,儿子进入军校走上了父亲的道路,开篇父亲与儿子肉身的互动让观众产生了“邪恶”的想法,但这是父亲在安慰受噩梦困扰的儿子,缺失的母亲让这个家庭残缺,想要在残缺中寻求安全感是父子两人以及每个残缺家庭需要费力争取的良药。
相依为命也是这个境遇下被不断提及的饱含悲情色彩的词语。
儿子的女友在军校里与他分手,一个在屋内,一个在窗外,女友没有进入屋子,儿子没有走出屋外,而窗户只是打开了一条缝,这段分手戏让人印象深刻,进不来出不去,而父亲则一直在屋内。
父亲的肺部透视片始终在提醒着生命的衰落,儿子的健身则是生命力蓬勃的展现。
与这对父子相反,父亲战友的儿子则是失去了父亲的孤独者,他的父亲在战争中死去,这个秘密被一直保守在儿子父亲的心里。
他们都被缺失的家庭角色所困,但又不尽相同,缺失父亲得孩子在性格上是更柔弱温吞的一方。
最后儿子与父亲在温情暧昧的凝视与互动后各自回房睡去,父亲做了一个冰天雪地的梦,他们曾经的房顶后花园由金黄色变成了白色,不再有那盎然的生机。
他们离不开对方,却不得不离开,儿子像死去的母亲一样漂亮,但终究要拥抱独立于原生家庭之外的人生,父亲也终究要拥抱依旧残缺与孤独的余生。
5 ) 他们是父子,他们像兄弟,他们像情人
索库洛夫(A.Sokurov)的电影《父与子》,始于父与子的一场同床异梦。
他们深切地爱着对方,但是儿子的梦中没有父亲,一个人的荒芜。
他们的这场床戏展示在电影的开始,似乎在告诉我们,这场貌似父子“做爱”(实际上可能是在挣扎于一场噩梦)的情节在毫不犹豫地隐喻着什么。
有人说这是俄罗斯对于苏联的一场难以割舍、却不得不分离的政治隐喻。
不管在政治上具体隐喻什么,父与子之间的关系都是隐喻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音与画是间离的,他们各自的梦中都没有对方;他们在逼仄的空间呈现出那么强烈的依恋,而我们在强烈的依恋中时刻都感受着纯粹的父子之爱中的挣扎,正如阿列克谢所说的那样:“一个父亲的爱是如此折磨人,一个爱他的儿子让自己受折磨。
”这是俄罗斯人的基督教哲学。
从狭窄逼仄的空间,到爬满电车铁轨的街道,再延伸到远处的城市建筑群,我们隐隐能看到那些能树立威权的大建筑,那仿佛是一场遥远的梦,而他们的挣扎,只是在逼仄生存空间外的一场屋顶的游戏和亲密。
电影依旧是俄狄浦斯式的,儿子阿列克谢在進行一场逃离父权的努力,对于父辈代表的历史记忆的窥探和回避。
他们之间借助了父与子同性恋的乱伦关系,展现了性紧张所代表的政治紧张。
电影最大程度地抽离了故事的可能性,克制的镜头语言演进着一个谜一样的梦魇。
借助柴可夫斯基的配乐,让心理空间和现实空间充满了挣扎与融合的尝试,就像父与子之间的同性感情。
《父与子》充斥着强烈的同性恋隐喻。
《父与子》中的父子既迷恋又拒斥。
真实的外部环境显得迷离而模糊,但是人物的美,通过特写镜头,引发人的欲望。
父与子之间的胶着,传达出强烈的罪恶感。
儿子看着父亲的照片,那是医院照出来的胸部的X光片,不再是衣物遮挡,也不是肌肉遮挡,似乎更加能赤裸裸地分析其本质了。
儿子分析父亲说:“最漂亮的是你,像一棵树,你的两腿是树根,胸脯是树干,双臂是树桠。
”儿子面对父亲,摸了摸父亲,又摸了摸自己,说:“我们两个好……好不一样。
”“你以后会喜欢的,我也是……”儿子说:“这就是你对我所有问题的答案?
”父亲说:“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
”父与子每个人都藏着深深的焦虑,他们是那么一样,又是那么不一样。
同性恋的身份焦虑,明显有着政治身份焦虑的隐喻。
“一个父亲的爱是如此折磨人,一个爱他的儿子让自己受折磨。
”折磨与煎熬,是他们共同的心理。
这对“仿佛受到了诅咒的”父与子,再也找不到他们的情人和母亲,那个更加古老的俄罗斯母亲,或者他们灵魂上的圣母玛利亚。
他们都梦魇住了,不敢肆意睡去。
他们不仅仅是同性恋,而且还是父子,于是折磨与煎熬就更加深。
他们互相爱,又挣脱不开。
电影不仅展示了一对父与子。
还有一位寻找父亲的年轻人。
寻找父亲的人,想知道为什么父亲会和母亲离婚。
父亲去哪里了,他为什么会失踪,是不是因为父亲杀过人。
他不相信父亲杀过人,即使杀过,他也会和父亲站在一边。
对于逝去的东西的留恋。
或许是指苏联。
不管苏联有没有犯过巨大的政治错误,他都想了解并亲自见识。
这是一种逝去的诗学。
他们隔壁,深深的房井另一面,住着他的邻居,年轻男人萨沙。
“到外面去!
”三个年轻人,在一条架在屋井上的悬空的木板上,互相打闹。
阿列克谢对萨沙说:“永远不要害怕任何事情!
”阿列克谢,萨沙,和寻找父亲的年轻人,开始一起和父亲对峙。
父亲因为危险,教训起了儿子。
三个年轻人开始对付父亲。
“外面”和“风险”,成为父与子之间对峙的导火索。
或许这是新的俄罗斯开始对老苏联产生强烈的敌意。
年轻人开始呼唤父亲的回归,不管父亲有没有罪恶,不管活着的父与子之间的爱多么有罪恶感。
那个寻找父亲的儿子,并不知道他父亲的故事。
他的父亲是接到命令并唯一存活下来的人,他想杀掉那个给他下达命令的人。
我们只能从父亲的口中知道这是98年,但是我并不知道具体在影射什么政治事件。
但是,两个年轻人,乘坐城市的有轨电车一边游览城市,一边回忆他的父亲。
这时候列宁格勒的城市全景一收眼底。
他们在谈论《浪子回家》的寓言故事。
他们谈到了冬宫镇馆之宝,伦勃朗的那幅《浪子回家》(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这是一个圣经题材故事,以一个大家门户的前厅为背景,画中的老人已是风烛残年,疲弱的视力已不能帮助他更好地辨认面前的情景,他伸出双手接受失而复得的儿子,那双颤动的手在儿子的背上抚摸着,生命的源流在那儿奔涌着。
衣衫褴褛的浪子身上留下了流浪的印记:他挥霍尽了向父亲索要的资材,时逢歉年,受雇为人放猪,食不果腹,饲料充饥尚求之不得,遂念及家中无尽的好处,回家跪在老人的面前,说道:“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作你的儿子。
”源远流长的微波细水汇入生命的活体,一脉相承的最初时日又回到身边。
寻找父亲的儿子说,为什么是儿子回家?
应该是父亲回家。
因为儿子知道应该往哪里去,他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
我们或许更加清晰地猜想,父亲已经挥霍尽了资材,应该回归这里,向儿子下跪说:我不配称作你的父亲!
俄罗斯又找到了她延续了千年传统的路。
奇怪的是,2003年,也就是和《父与子》拍摄的同一年,安德烈·萨金塞夫俄罗斯就展示了他的“浪子回家”的故事,电影《回归》,让一个离开多年的父亲回到了家乡。
同样受塔可夫斯基影响的《回归》,和《父与子》有着相同的政治隐喻。
《回归》重新肯定及延续了塔可夫斯基所代表的俄国电影思维。
它同样讲述的是父与子的关系。
离家十多年的父亲突然归来,打破了两兄弟的和谐生活。
他们既对这个陌生的父亲充满怀疑和好奇,又对当年他突然抛开母亲而耿耿于怀。
第二天,父亲带着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找寻一些东西。
在路上,小伊万开始表现出对父亲的不满,认为他们没有父亲的生活也过得很愉快。
他们来到一个大湖,父亲带领两个孩子做了一艘小船,驾船来到一座神秘的小岛上。
父亲和两个孩子分开,两个孩子出去捉鱼,父亲去找些东西,孩子们回到与父亲约会的地方时已经非常晚了,父亲大发雷霆,愤怒地责备哥哥安德烈,伊万哭着爬上一座高高的废弃的铁架上。
父亲怕他发生危险也追了上去,结果父亲失足坠亡。
两个孩子把父亲的尸体运回湖岸,就在他们启动汽车,打算把父亲的尸体装进去时,父亲的尸体连同那条小船慢慢地沉下湖心。
“一个父亲的爱是如此折磨人,一个爱他的儿子让自己受折磨。
”儿子阿列克谢对城中的女友这样说。
他把要来的项链又还了回去。
“受折磨的爱意味着你们并非相等。
你们不是兄弟。
”女友说。
阿列克谢说他梦见了父亲,又梦见了他和女友的儿子。
女友说他还没有准备好要儿子。
她对于阿列克谢并没有信心。
他连身份都不确定呢,也没有从父亲的爱中独立出来。
父亲说,对于你来说我就是兄弟。
阿列克谢不想知道他的童年,那只是父亲的回忆。
这意味着他们要分道扬镳。
他们并不分享共同的记忆了。
他们应该共同建立美好的记忆,共同建议一个安全的堡垒,就像他们再次来到外面的房顶,整部电影父与子之间的美好达到了高潮。
他们不是兄弟,他们是父子,但是他们仍旧可以平等,可以分享共同的美好记忆。
阿列克谢发出了他的宣言:“她想什么,她要什么,我都不感兴趣。
她从来不了解我,我不需要她。
”儿子骑在了父亲的肩膀上,他在飞翔,借着父亲强有力的肩膀,飞得更高。
他要离开这里,离开父亲。
他们各自寻找自己的幸福。
儿子说:“我的话对你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儿子像是在试探父亲的心意。
父亲说:“你看上去,就像你的母亲。
上帝把你赐予我,你的一切对我都很重要。
”父亲回报了儿子的心意。
阿列克谢对父亲说,这是萨沙,我爱他。
萨沙对阿列克谢说,他想住到他们家中。
阿列克谢说,你就住在隔壁,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这又是苏联解体后的寓言。
父亲和儿子各自睡去,分别在自己的床上。
父亲梦到了儿子的梦,那片荒原,儿子不在那里。
儿子也梦到了父亲的梦,梦中下雪,父亲就只穿一条单裤,孤独地在冰天雪地中,坐着,那么冷。
他们分开了,却共享了同一个梦境,精神已经融合为一体了。
他们冲破了多么大的隔阂啊!
6 ) The love That Crucifies
看索库洛夫(A.Sokurov)的电影《父与子》。
现实里美丽的里斯本幻化为军港圣彼得堡,相依为命的父子也脱离了一种具象的刻画而成为理想中的活物。
父亲是退役军官,儿子是士官生。
父亲总是安抚从轼父暗示的噩梦中醒来的儿子。
儿子的女友意识到自己的旁观者身份决定离开,父亲则永远沉浸在丧妻的悲哀和战争的伤痛里。
论者都提到了电影中的性暗示,可是索库洛夫拒不承认。
我相信索库洛夫是完全正确的。
同性恋男子往往与母亲有着非常强的认同和亲近感并与父亲疏远,但异性恋男子与父亲的关系会很分化。
一个极端是无沟通,另一个就是完全的理解和体认。
影片中的关系属于后者。
阿列克谢(儿子)用指头触摸父亲的太阳穴,然后回头丈量自己,发肤受之父母的感恩之情就很了然。
父亲安慰噩梦中醒来的儿子,意识到噩梦也是儿子对父爱拒斥的表现,那种两难的境地也是真实的。
父爱在电影里既是过度的保护和宠爱(阿列克谢在窗外做危险动作被父亲当着朋友的面责打),也化身为责任感和期望(父亲在军校骄傲地观看阿列克谢格斗)。
我们都在这纯粹的父子之爱中败退,正如阿列克谢所说的那样:A father's love crucifies. A loving son lets himself be crucified. 俄罗斯人深刻的基督教哲学居然从这里浮出来,我只能赞叹。
神将自己的独子耶稣献出来救赎,而耶稣则从容地赴死。
道成肉身的那一刻就是十字开始淌血。
爱,不论亲情爱情,都是布满了十字的(crisscrossed)。
父亲认识到阿列克谢重要走出自己的生活,自己也会老去,死掉。
阿列克谢也需要自己独立的人格。
可是相依为命的生活就是如此,这样的爱是伤害爱者的。
可是阿列克谢与父亲是亘古的,他让父亲想起自己一生唯一爱过的女人,因为阿列克谢的面容是她的,这是血脉的亲情。
阿列克谢唯一感到安全的地方也是父爱。
父亲总觉得自己的肺有问题,军医学生阿列克谢每天拿着父亲的胸透片研究。
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阿列克谢在邻居面前小孩气地说:这是我的父亲,我非常非常地爱他。
最后的场景依然是睡梦中的父子。
父亲梦见的是雪,也即是死亡。
向死而生的父亲和生命初始的儿子,如何梦下去?
可以自己想象了。
7 ) 碎感
全片暗流涌动又波涛汹涌父亲的爱总是让人备受折磨令人备受折磨的爱说明你们本就爱得不平等在欲望出现的时候,转身 赶快逃离影片演员的讲话就如梦呓耳语一般,直直得钻进你的心里,让人一点防备都没有。
全程暖色调,节奏缓慢,画面像油画般美丽,像诗一般缓缓流动。
有种看懂了又什么都没懂的感觉,觉得影片文艺性文学化很强。
看的时候父子两人多次的近距离接触,或许是受到“同志”标签的影响,我总有着快亲上去啊,好像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按捺不住做一场爱一样的期待。
但看完再想想或许是受标签的影响有些大了,看到一些影评里导演说“他们只是比一般的父子更亲近些”,嗯是这样吧。
第一次看意识流类电影(应该是意识流吧…?
)没有觉得闷,全程都有一种你已进入剧情已深入到父子俩全部生活与琐碎的内部中心的感觉,但你回头一看却发现自己仍在尽力攻破外面那层薄薄的壳,犹如隔靴搔痒自我安慰却又无可奈何。
所以我究竟看懂了吗?
关于开头勾人浮想的喘息与两个抱在一起的美好肉体(应该有穿短裤),一开始我也在发挥想象力两人在做爱,但看完以后又觉得不对劲,全片都极隐忍克制 虽有暧昧但又不完全同于那种爱欲性欲,所以父亲只是在安慰拯救陷入噩梦梦魇的儿子,“他们只是比平常的父子更亲近些”。
开头和结尾都以梦境,都是一方问另一方,“我看到那条路了,很美”“我在那儿吗?
”“不,没有,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两个互相依恋依偎的人,终究还是要面对没有另一方的环境,不管是现实的以后还是甚至在梦里。
“我会离开,你会再结婚”不知道父亲和儿子谁心里的失落孤寞更大些。
我也不知道我看了什么,写了些什么,导演讲了什么想向观众讲些什么……所以我到底看懂了什么又没看懂什么?
一切朦朦胧胧恍恍惚惚。
“比其他父子更亲近一些”所以有没有亲近到衍生出爱情与欲望?
现在我在想了:父母与子女之间会不会有爱情,能不能有暧昧有欲望?
那可能存在的真实的感情与道德批上的“乱伦”之间的天秤,你该给哪一方加上砝码?
8 ) 所有的镜头,都没有超过两张脸的界限。
一部影片花去我三份时间。
它太梦幻,人在现实里握手,幻觉已跑到远方,与人隔离。
它太暧昧,父和子都有一双忧郁的眼睛,如猫般敏感的表情,每当他们的脸部被特写,眼神被放大,我都不得不暂停,以使它冗长的叹息不会存留在我的脑子里。
它太不知所云,难懂的俄语,即使打上中文字幕也依旧难懂,儿子无法令父亲信服的情话,只能面对水流去说,父亲无法告知儿子的体贴,只能向着皑皑白雪去展臂。
中间的一段,我几乎用了快进,只想让它尽早结束。
其实,父子的题裁很有些微妙。
一方面,他们同性,另一方面,他们不伦。
但是,面对这样相互祝愿的父子,你能做出的批判都将溺死在嘴巴里。
连儿子都说,我毕业之后,我会离开这里,你不会孤单,你会结婚。
但之后的眼泪,依旧代表着爱情。
艰涩,又决绝。
它与我意想的,有所失望。
但也只能这样。
所有的镜头,都没有超过两张脸的界限,也到达不了两颗心的统一。
9 ) 非成熟的真实=解构主义
用开头骗我看完了。
不过对我的口味啊。
用画面(绘本:童年定住的幻想;故意出错:你要干什么呢?
)和声音(仅有主观需要的几种声音:梦境,定住的幻想。
)表现的梦境。
打破了所有的安全距离,是我所有的恐惧、被定住的白日梦、害怕被人看穿、害怕发生、害怕想起,但原来是有人和我一样在意的。
神经质小孩的专属生活原来过去 非成熟的真实 便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和过去的我一样年轻。
但现在的我能再一次拥有解构主义吗,还是只能有不耐烦吗。
我们不需要动脑子想,只需要反映脑中所映入眼帘的东西,我只会用笔写(高中的道顿堀白衣女人),今天知道居然可以拍 成如此的电影(在一个功利实务主义的人眼里的屁都不是可以变成千秋百态的津津乐道,虽然被否定刺痛被逼去成长但解构主义永远在我最深的心里,它不是可以被展示出来的东西,它是永远无法分享的孤独和胜利。
)如果和一个人在一起不开心,当然只有离开她
10 ) 异色的“恋父”乌托邦———《父子迷情》4星推荐
记不得是多久前看的这部电影,只是很讶异那种缓慢而唯美的情调,很讶异那对如天使般的两个年轻男子竟然是对父子。
从一开始,父亲去探望自己的军校的儿子,调皮而激动的心情像是在等待自己久未逢面的情人。
而儿子出现之后,两个人相对而视的表情让人感到一丝温暖和亲切。
那不是父子该有的表情,那是一对挚友方有的心心相印。
想要从电影缓缓流出的情绪中看出什么情节是徒劳的,总结下来,我印象中只有这么几个简单而悠长的片段:父亲在屋顶锻炼,儿子喜欢和他在屋顶踢足球,儿子的朋友从远方来二人在小城内四处闲逛,儿子和女友分手伤心欲绝。
似乎导演不急于想告诉我们,只是想让我们静静地享受着这如水晶般透明的情感。
一切猜忌和暧昧都是有心者的自我意淫。
那对父子就是父子,如同《吉莫尔女孩》里的母女,即使再亲密,也终究是单纯的母女感情。
只是这份爱太平等太美好,让人无法相信而已。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男人都有恋母情节,但是我曾经就很怀疑:难道男人就没有恋父情节?
此话说起来好像极为好笑,很多儿子对父亲的记忆好像只有反抗和叛逆,何来恋父?
但是如果你们仔细想想的话,哪个儿子不曾暗暗为父亲的一句无心的夸奖而欢喜?
哪个奔赴沙场杀敌的男子汉不曾在心底希望得到父亲对自己男人身份的认可?
金庸小说里曾经出现过一种爱,是郭芙对杨过的“仇恨之爱”,这种看似对立,其实质却是内心无法阻止的一种强烈感情的极端流露。
这种爱恨不分的情况,在父子之间似乎更容易得到印证。
俗话说关心则乱。
越爱一个人,就会越想得到一个人的注意,而失败的结果就越容易转化成一种类似于“恨”的爱。
当你狠一个亲人时,那多半因为你曾经或仍然太爱他。
所以才久久不能原谅。
相对凡俗的父子对抗之爱,《父子迷情》似乎是父子爱的乌托邦,你可以看见父子间的敌视和拌嘴,也可以看见儿子对父亲的不屑和反抗,但是除此之外,夕阳余辉下两个像朋友、恋人般依偎的父子却是世间少有、人间难寻的。
也许,这也是这部电影饱受争议,并奇特的被列入“异色”氛围的原因吧。
影片的画面像极了一幅中世纪浓彩的油画,人物完美的体型如同移动雕塑般在咖啡色的夕阳中尽情展现。
而小电车、缓慢移动的镜头也让人仿佛置身于无人的世外小镇,悠远而忧伤。
电影在冬天结束,那个天台瞭望着一片灰色并满是雪花飘舞的海,那情景曾经出现在我的梦里。
那是一种梦境的真实展现。
但是父子之间其特而如母子般的感情,又何尝不是一种梦境呢?
以此文献给8月8父亲节。
迟到的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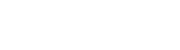





















第三季这么快